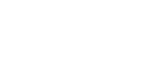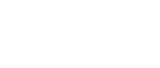折西小记
| 招商动态 |2016-07-30
这次没时间找图,直接附视频,见文末。
距离上次公众号更新已5个月余。这大半年的时间,足以让公众号“长草”了,倒也呼应现在甘孜州折多山以西的风景。从石渠的扎溪卡草原、德格的阿须草原,再到理塘毛垭草原以及康定的塔公草原,放眼望去,都是一片怡人的绿。高原特有的高山草甸,在这个时候就像抹茶班戟一样,偶有几座雪山,也似抹茶班戟上的糖霜。
沿着318国道,从东向西依次可以领略到大渡河的奔腾、二郎山的惊险,情歌故里的繁华、茶马古道的传承。从康定折多山往西而下,便到了摄影天堂新都桥,这是康南康北分路的岔口。南路是318的延续,经过天路十八弯,穿过高尔寺山,就可感受到雅江西俄洛的硬朗刚俊、理塘天之城的纯净无垠、巴塘藏江南的民国遗风。自此,金沙江由北向南隔断康藏,对岸即是西藏昌都的芒康。北路一路向北,可逐一抵达“菩萨喜欢的地方”——塔公草原、莲花宝座般的雅拉雪山、八美的土石林、道孚的藏民居、炉霍的蹦柯房。此后进入317国道,往北翻过老折山则是色达金马草原,往西绕过卡萨湖、盘过罗锅梁子,就到了康北粮仓——甘孜县,这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地方。从甘孜县继续向西,到马尼干戈分路,再北上就是四川最高的县域石渠(海拔4200m),往西去需翻过川藏第一险——雀儿山才能到康区四大土司之一的德格土司故地,德格的印经院奠定了其跻身藏区三大文化中心的地位,藏族史诗英雄格萨尔据传也是出生于此。从德格走森林公路——柯山路即可到白玉县,白玉河坡打造的藏刀历来为藏区之最。而从甘孜县往南,就到了阿来笔下的瞻对故地——新龙。在100多年前,这里出过一个叫做布鲁曼的头人,带领新龙群众冲破土司和拉萨政权的封建统治,要把布达拉宫的柱子当作自己的拴马石。正因为这个地方的骁勇剽悍,使得原来格鲁派政教势力深入不了,因此,新龙是甘孜州唯一没有格鲁派(俗称“黄教”)寺庙的县。
如果按照上述的交通路线走,甘孜的大部分地方都能抵达,只剩下东部挨着阿坝州大小金川的丹巴,古碉、藏寨、美人谷是她的名片;还有西南部挨着云南迪庆的乡城——香巴拉,该县的青德镇被誉为高原托斯卡纳;稻城(亚丁)——最后的香格里拉,拥有三神山和状似飞碟的世界海拔最高机场(4211m);得荣——太阳谷,金沙江第一湾即在此;以及靠近四川凉山州的九龙——“酒的故乡、龙的传人”,该地以种牦牛、花椒出名,也以爱喝、能喝、敢喝酒为人乐道。
以上是甘孜十八县风土人情略述。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见闻和思考。
一、复仇
在康区部分地方,至今还存在着血亲复仇现象。如A家人害了B家人性命,哪怕A家的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并给予了B家人赔偿,B家人仍会以A家人的性命相偿,且将B家人赔偿原封不动返还。这不禁令人想起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件”。由此引发的一个思考是,国家作为超然的第三方,是否天然地对其所辖地域上的民众垄断司法权?这种现象不单存在于康巴藏区。就晚近而言,闽粤沿海地区,如漳泉潮汕等地,在明清两代直至民国,都出现过群体性械斗、命案最终由宗族仲裁调解的案例。其中的最终司法权表面上也许由国家行使,但民间(即社会层面)还有另外一套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并没有直接反对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但实际上却挑战了这种垄断。而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正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不管是民国还是共和国)。虽然早在秦汉,司法权的垄断便逐渐收于象征公权的朝廷(游侠渐不见容),但直至民国建立前,还始终存在一自治的乡绅阶层,就康区而言,寺庙的高僧大德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汉地的乡绅。严格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使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逐渐形塑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有别于传统“天下”的“国家”。也正如此,在不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变革过程后,这片土地及其之上的人民逐渐(自觉不自觉)地被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机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反过来坐实、丰富和扩展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所以,康区的复仇现象,从社会学角度看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从政治学角度看至少体现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根本就是由谁来垄断暴力、司法以及相应地被称为“统治机器”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工具。
二、信仰
藏民族一直为外界所知的是其对藏传佛教虔诚的信仰。而信仰分知其所以而信与不知其然也信。前者是理性思考选择后的信,后者则颇似盲从的迷信。纵观世界几个大的宗教之发展,大体上都是从理性选择后的信,到后来不知其所以然的信,这个演变过程伴随着的是信教群众逐渐增多。宗教发展的一开始,越是口号简单、意思简练,才越能吸引更多人加入进来。以佛教背后哲学思想的精深,如果要求每个信教的群众都严格按照相应的学经习法程序,自然很难吸引更多的群众。因为群众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如果大家都不事生产,无从供养,如何支撑精神修习?所以,藏区群众的所谓“信教”,自然不是要求普通群众像僧侣那样持戒精修,而更多的是把佛教的思想教义通过外在形式渗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自觉直至变成不自觉和自在。当这种“信仰”逐渐变成社会习俗和“制度”后,就容易演化为对“制度”的迷思。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群众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本身,而是“耳朵”和“脸面”(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信教群众是出于纯粹的宗教情感,如对死亡的畏惧、逝者亡灵的超度而自发供养寺庙僧尼)。比如,很多藏族老乡大概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有这样那样的行为准则和约束,但不遵守就会受到舆论和集体的反对、制裁,或者是消极的无形的隔离,给自身带来不好的名声,甚至只能远走他乡,这就是担心其他人的“耳朵”。又比如,这家人到寺庙作布施,隔壁人家也要去,还要争取比他布施得多,这样才能体现更虔诚,也更有“脸面”,在当地就会更受尊敬。可见,“信教”的群众不能离开物质,也难以脱离社会及其约束。有一种说法是,藏民族是精神最富有的民族,但并不代表这个民族就是对物质追求最少的民族。与其说是精神追求让其减少了物质需求,不如说是自然环境让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物质,或者说不是因为追求少,而是还没有尝过物质丰富的滋味。况且,这种物质丰富与精神追求本质上并不天然对立,如果对立,那传统的寺庙与信徒的供施关系和背后的逻辑意义便说不通了。
三、扶贫
未来五年,扶贫攻坚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既体现了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更体现了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因此,其世界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这么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和转移,以政党和国家的名义和形式来做,是史无前例的。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的政党,而不是部分利益的“part-y”。具体到基层,扶贫工作实践可谓千姿百态,地方政府识别贫困的方法更是被生动地概括为“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无读书郎”。党委和政府让群众脱贫的途径根本上就是两条:输血和造血。前者是短期、见效快、不可持续,后者是长期、见效慢、可持续。在藏区,面对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现实,脱贫工作更加艰巨。依靠“输血”,尽管可以在面上脱贫、数据脱贫,实际上是一种“被脱贫”,不是治本之策。特别地,党委和政府的扶贫专项资金,因政策规定必须直接下发到老乡手上,往往使得扶贫资金化整为零,每户家庭拿到的是不多的资金,且更多用于直接消费而不是积累再生产,难以发挥资本集聚效应,这使得“输血”效果仅仅局限于一次性的保障,难以和“造血”联动,也容易滋生群众“等靠要”思想,增添“造血”思想障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因为信教的原因,很多群众拿到各种转移支付资金后,转手便交给寺庙作布施,以求积功德、增福报。曾听到本地干部如是说:“佛教讲的是感恩积善得福报,老乡拿政府钱去供寺庙,要修功德,却不知自己应该感恩的是给他们钱的政府,不感恩政府,算是积善得福报吗?”这话直接点出了信教群众的“形式盲从”。佛教讲修行才能得大智慧,这种修行不是单纯念一亿遍经能修得,也不是单纯作大额布施能修得,而是从自救开始。佛教讲利他、去无明、得解脱,不是光靠转经,而是要劳动,要能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至少不给他人添麻烦。搞经济、搞民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利他,一种修行?反观寺庙,寺庙拿供养的钱却无法帮助这些信教群众解决吃饱穿暖问题,这恐怕也不是佛教教义所倡导,遑论“利众生”。因为高寒高海拔,自古藏区群众(包括僧侣)就以食牦牛肉为生,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寺庙不能一方面让百姓“戒杀生”,一方面又要百姓供奉“好牛肉”,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荒谬之至。“戒杀生”的后果不仅使得群众无法将可出栏的牦牛拿到市场上变现从而创收脱贫致富,而且还造成草场资源减少,破坏原本平衡的生态链,导致包括人在内的其他动植物受到威胁,进而影响整个雪域高原的生态安全。从这个角度看,这恐怕不是佛教教义所宣扬的。可见,宗教一旦被“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所裹挟利用,不仅难以自立自持,还可能制造危及人和自然的祸端。
四、建设
有干部形象地概括了在藏区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子登科”:修路子、盖房子、看庙子、举杯子、发票子。目前甘孜州还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在这个与山东省面积一般大的地方,交通建设是发展的必须也是首要。十分可喜的是,经过三年交通大会战,甘孜州十八个县均通有国道、省道,325个乡镇也都实现硬化路全覆盖。“发票子”和“盖房子”和主要体现的是民生方面,涉及的是给群众发放各项补贴(如退耕还林、还草)、扶贫专项资金和帮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举杯子”说的是招商引资;“看庙子”则指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这个“五子登科”的概括应该算是比较到位的。值得一提的是“盖房子”。前面讲精准识别贫困的办法是“四看”,而脱贫的标准则是“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因此,要让老乡们脱贫,让他们住上好房子是首要。党和政府通过补贴、优惠贷款和群众自筹等方式帮助老乡盖房子,但藏族老乡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房子盖得越大越好,楼层多为2-3层,有的藏房占地面积达300余平方米,还不包括房子前的坝子。一旦房子盖大了,预算就要增加,有的老乡因为把资金都用在扩大面积上,没有后续资金装修,结果还不起贷款形成银行坏账,也出现了因“盖房子”而导致返贫的现象。对此,有的干部做老乡们工作,建议先修一个小房子,等资金充足了,再修一个,也可以形成一个大院子。但还是有不少老乡想不通,硬是要修大房子,显得气派有面子。这种对物质和世俗的追求,似乎与轻物质的藏传佛教信仰相冲突,体现的更多的是人性。因此,宗教信仰在大多数藏民心中确实根深蒂固,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这并不代表藏民就不追求物质。对藏民重视精神信仰而轻视物质追求的印象,可能更多来自外界人的想象而非现实。另外,甘孜十八个县的建筑风格也各有特色,比如丹巴古碉藏寨、道孚民居、炉霍崩柯房、新龙土堡、乡城白藏房、雅江黄藏房、稻城方石黑窗房,新都桥的房子则以窗户大且多而闻名,屋顶多采用汉式屋脊筒瓦,给人以穿藏装带斗笠之感。有时间会另开一篇介绍甘孜十八县建筑。
行走在康巴高原上,映入眼帘的除了雪山草地,最多的就是信号塔和输电设备。因此,最令我敬畏和震撼的并不是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特别是路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们。这是现代文明的力量、是科技的力量、是改造自然的力量、是人的力量。对于藏区的建设们来说,他们可能会比内地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和健康考验,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建设们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干的是革自己命的事业。一代一代的建设们就像那高原上自由奔跑的牦牛,只要吃点地上的草,就能迸发刚劲而不知疲倦的生命力;又像那盛开的高山杜鹃,哪怕海拔再高,依然可以绽放地如此热烈。
最后广告一下,8月9日,康巴艺术节、康定情歌音乐节、甘孜国际山地旅游节“三节”开幕,欢迎广大朋友来没有雾霾的地方洗洗肺、爬爬山(贡嘎雪山),唱情歌、跳锅庄。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